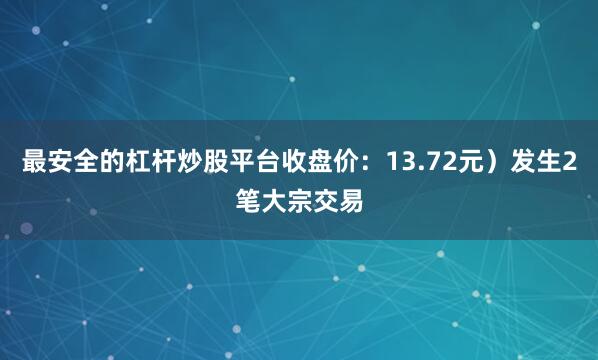图片
天时与地利:鲜卑南迁背后的无形推手揭开嘎仙洞的秘密,我们找到了鲜卑人历史舞台的起点——大兴安岭。但这群生活在山林与草原边缘的民族,并非一开始就想着去逐鹿中原。
他们安稳地生活了数百年,是什么力量像一只无形的大手,最终把他们推向了历史的前台?答案藏在两个看似枯燥却至关重要的词里:地理与气候。
舞台:大兴安岭的独特地位
看一下中国东北的地形图。大兴安岭,这条绵延上千公里的巨大山脉(北起黑龙江,南至西拉木伦河,是内蒙古高原与松嫩平原的分界线),可不是普通的山。它扮演着一个极其关键的角色:
地理分水岭: 它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的分界线。山以西(比如呼伦贝尔草原、内蒙古高原),地势高,是游牧的天下;山以东(比如松嫩平原、辽河平原),地势低,是农耕的乐园。同时,它也是中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,意味着山的东西两侧,降雨量差异巨大。文明的十字路口: 它的东边,是富饶的松嫩平原,连接着更广阔的东北平原;它的西边,是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,再往西就是浩瀚的蒙古草原。简单说,向东,可以走进农耕世界;向西,可以融入游牧帝国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(Fernand Braudel)曾提出一个精辟的观点:山地往往人口过剩,或者对它的财富来说,至少是人口过多。
因此,山区必须周期性地向平原倾泻它过多的人口。 大兴安岭,正是这样一个需要“倾泻”人口的山地环境。对于生活在这里的鲜卑人而言,向东,他们可能被农耕文化同化,成为新的农民;向西,他们则可能成为草原上新的霸主。
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说得更形象:大兴安岭是鲜卑等少数民族“一个幽静的后院”,呼伦贝尔草原是他们的“历史舞台的后台”,而蒙古草原则是他们真正的“历史舞台”。呼伦贝尔草原不仅养育他们、武装他们,更是他们由东向西,征服更广阔世界的起点。
图片
关键推手:气候的“上帝之鞭”
如果说地理提供了舞台和路径,那么真正抽响鞭子、催促鲜卑人动身的,是气候。这里必须提到一位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——竺可桢先生。他通过研究古代文献、物候记录等,复原了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曲线。他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:
漫长的寒潮期: 从东汉初年(大约公元1世纪)开始,一直到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时期(大约公元600年),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一个持续时间特别长的寒冷期(竺可桢划分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中的“第二个寒冷期”)。寒冷期对草原意味着什么?
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:
牧草枯黄:气温降低,降水减少,会导致草原生长季节缩短,牧草产量和质量大幅下降。牲畜遭殃:没有足够的优质牧草,牛羊会变得瘦弱,抗病能力差,容易在寒冬中大量死亡。严寒本身也是牲畜的杀手。生存危机:对于依赖畜牧业的游牧民族来说,牲畜就是他们的粮食、财产和生命线。牲畜大批死亡,意味着整个部落面临饥荒和生存危机。对鲜卑人意味着什么?
他们生活在蒙古高原东部边缘,首当其冲:
草原承载力的崩溃: 原本能养活大量人口和牲畜的草原,因为气候变冷变干,变得无法承载。为了活下去,他们必须寻找新的牧场,寻找更温暖、水草更丰美的地方。向哪里找?答案显而易见——向南!向着相对温暖、靠近农耕区的漠南(阴山以南)草原,甚至是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。寒冷不仅打击草原,对农耕区也有影响(比如粮食减产),但程度相对较轻。更重要的是,中原地区积累的财富、先进的物质文明(布匹、粮食、铁器)对资源匮乏的草原民族有着巨大的吸引力。当生存成为第一需求时,劫掠富庶的农耕区就成了一种本能的选择。图片
地理与气候的合谋
于是,地理空间和气候变迁这两股力量合谋,共同导演了鲜卑人的历史走向:
大兴安岭西麓的鲜卑部落,更容易向西进入呼伦贝尔草原,进而挺进广袤的蒙古草原,与盘踞在那里的匈奴等强大游牧帝国争夺生存空间。而大兴安岭东麓的部落,则可能向东进入松嫩平原,与当地的扶余、濊貊等农耕或渔猎民族融合或争战。持续的寒冷像一条鞭子(史家称之为“上帝之鞭”),抽打着草原上的游牧民族,迫使他们离开日渐凋敝的故土,向南、向西、向东迁移,寻找生机。 无论是向西进入蒙古草原,还是最终南下逼近长城,鲜卑人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与南方的强大邻居——中原农耕王朝(东汉、魏晋)——发生激烈的碰撞。翦伯赞先生一语道破天机: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一群牧人,而是“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、战士”,他们“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,走进黄河流域”。历史的交汇点
因此,当鲜卑人最终出现在老哈河(今内蒙古东南部、辽宁西部的一条重要河流,西辽河南源)和西拉木伦河(今内蒙古东部、吉林西部的一条河流,西辽河北源)流域时,他们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:
这里靠近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分界线——那道著名的秦长城和燕赵长城。正如《辽史》概括的那样:长城以南,是“耕稼以食,桑麻以衣,宫室以居,城郭以治”的农耕世界;而长城以北的大漠之间,则是“畜牧畋渔以食,皮毛以衣,转徙随时,车马为家”的游牧天地。这是“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”。无形的巨手
所以,鲜卑族轰轰烈烈的南迁史,绝非仅仅是某个英雄首领的雄才大略,其背后是地理环境的塑造和气候变迁的残酷推动。
是大兴安岭独特的枢纽位置,为他们提供了迁徙的路径和选择的可能;是东汉以来那场持续数百年、冰冷刺骨的寒潮,像“上帝之鞭”一样,抽打着他们离开故土,去寻找生存的希望。在这股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,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在长城沿线的碰撞与融合,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。鲜卑人的故事,从走出山林开始,就注定要与中国历史的主线紧密交织在一起。
鲜卑:
鲜卑人从哪里来?一场跨越四十年的考古大论战。
谁能想到,“鲜卑”这个霸气的名字,最初竟是指一条腰带?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茂林资管配资,股票配资排名,九鼎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配资股票户网一枪就把俩绝世猛人的兵器挑开
- 下一篇:没有了